2025年8月29日,国际肺癌研究协会(IASLC)主办的播客节目“Lung Cancer Considered”第311期正式上线。本期节目由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苏春霞教授担任主持,特邀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科吴楠教授、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朱正飞教授,围绕一例III期非小细胞肺癌(NSCLC)的真实世界病例展开深入的多学科讨论(MDT)。专家团队聚焦纵隔侵犯的精准评估、侵入性分期的价值、手术可切除性的界定、新辅助/辅助治疗策略的选择以及寡转移病灶的处理等临床核心议题,为III期NSCLC精准诊疗提供实操参考。“肿瘤界”特整理访谈精粹,以飨读者。

播客音频
访谈精粹
苏春霞 教授
大家好!本期MDT讨论聚焦一例真实世界III期NSCLC患者,病例情况:52岁男性,不吸烟,因持续咳嗽(抗生素治疗无效)就诊,胸片提示左上肺6 cm肿块伴纵隔侵犯,进一步CT显示肺门、纵隔淋巴结肿大;无基础病史,健康状况良好;脑MRI未见转移;CT引导下活检确诊肺腺癌,18F-FDG PET-CT下左上肺肿块呈高代谢,左肺门、气管旁淋巴结轻度代谢。
首先请教吴教授:影像报告提示纵隔侵犯,按标准可能分期为T4,但T3与T4的界定直接影响治疗决策。从胸外科视角,胸部CT评估纵隔侵犯的可靠性如何?是否需要补充其他检查?
吴楠 教授
苏教授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准确判断T3与T4。肿瘤最大径在5-7cm本属T3范畴,若出现纵隔侵犯则升期为T4(纵隔侵犯是T4的重要标准之一),此时准确评估病理分期对治疗方案的选择至关重要。
从文献来看,纵隔侵犯分两类:一类是仅侵犯纵隔胸膜或脂肪组织;另一类是侵犯心脏大血管、气管、食管等重要结构。2013年Journal of Thoracic Oncology的一项日本癌症登记数据显示,T4患者中约15%为纵隔脂肪侵犯,45%为重要结构侵犯,但两者生存预后无显著差异,因此临床仍将纵隔侵犯整体归为T4。
再谈CT的可靠性:CT虽像是“肿瘤侦察雷达”,但其并不完全准确——CT判断纵隔侵犯的敏感度约61%,特异度约79%,常存在高估或低估侵袭程度。打个比方,CT显示肿瘤“贴靠纵隔”,可能只是“两张纸叠放”(未粘连),而非“胶水粘住”(真侵犯),无法明确肿瘤是否真正侵入纵隔组织。
因此,临床需结合其他检查佐证:一是PET-CT,主要用于评估淋巴结转移,但对纵隔侵犯判断帮助有限;二是MRI,其软组织分辨率更高,像 “高清探测仪”,能更清晰显示肿瘤与纵隔结构的间隙(如脂肪间隙是否消失),判断T3/T4分期的准确率达80%-100%(CT仅60%-70%),尤其判断心脏大血管侵犯的准确率(66%)显著高于CT(50%);三是纵隔镜或EBUS,主要用于淋巴结活检,不直接判断肿瘤与纵隔的分界面。
最终常需综合评估,甚至手术探查,避免仅凭CT就武断放弃或冒进手术,从而影响后续治疗。
苏春霞 教授
感谢吴教授的详实解读。朱教授,该病例初步判断为III期,且PET-CT提示左肺门、气管旁淋巴结轻度代谢。从放疗科角度,您认为是否需要病理确认淋巴结状态?
朱正飞 教授
我认为非常有必要。现如今随着治疗手段技术进步,T分期可能已非手术绝对禁忌,而N分期(淋巴结状态)却更能预测患者能否从手术中获益。早年EORTC 08941研究定义“不可手术”时就提到:腺癌患者若存在任何纵隔淋巴结转移,即使技术上可切除,也不推荐手术,因这类患者从手术中获益有限。而若肿瘤虽大(5.5-7cm)但无淋巴结转移,说明其生物学行为以局部进展为主,恶性程度相对较低,此时积极局部处理(如手术)的价值更高——指南也明确,T4N0-1患者的手术指征更强,但若为N2,则手术推荐度显著下降。因此,明确纵隔淋巴结状态是决策的核心环节之一。
苏春霞 教授
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有时会跳过侵入性纵隔分期,但精准医疗要求我们尽可能明确分期。吴教授,您对EBUS和纵隔镜这两种常用分期方法有何见解?
吴楠 教授
分期的准确性是打赢肺癌战争的前提,治疗前分期就像战前侦察地图,跳过侵入性分期如同闭眼决策,隐患巨大。分期方法分为“无创”(PET-CT、脑MRI)和“侵入性”(EBUS、纵隔镜),后者是减少分期误差的关键——若仅依赖影像,约20%患者会出现升期。数据显示:CT显示淋巴结肿大且PET-CT阳性,转移概率约85%-90%;CT肿大但PET-CT阴性,转移概率约10%-15%;CT无肿大但PET-CT阳性,转移概率约70%-80%;CT无肿大且PET-CT阴性,转移概率约9%。
EBUS和纵隔镜各有优势,特异度均可达100%,核心都是获取淋巴结病理:
EBUS:创伤小,经气管镜操作,对气管旁、隆突下、肺门淋巴结穿刺,有经验医生的敏感度可达85%(ASTER研究证实其敏感度不亚于传统纵隔镜);术后当天可出院。
纵隔镜:需全麻下颈部小切口操作,直视下活检上纵隔、隆突下甚至肺门淋巴结,取样量更大,病理准确率高,还能为后续基因检测提供充足组织;但需住院,并发症发生率约1%(如血管撕裂),创伤比EBUS大。
临床实践中,EBUS已成为术前分期首选,纵隔镜更多用于“再分期”(如化疗后评估)。但近年免疫治疗兴起后,部分国际研究也用无创影像进行再分期,需结合具体情况选择。
苏春霞 教授
真实世界中,本例患者经EBUS证实11L、4L淋巴结阳性。对于III期NSCLC,MDT讨论的核心是“是否可切除”,吴教授,从外科视角如何界定“可切除”与“可手术”?对肺功能又有哪些要求?
吴楠 教授
这是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概念,需分开解读:
可切除(Resectable)侧重肿瘤本身:能否实现R0切除。取决于肿瘤大小、是否侵犯重要结构(如左侧锁骨下动脉、气管、食管等)、淋巴结状态(是否多站N2、巨块型或包绕重要结构)。比如肿瘤包裹主动脉或侵犯心脏,多数中心定义为“不可切除”,但部分局限T4(无淋巴结转移),联合心脏外科等多学科协作,也可能实现切除,因此“不可切除”并非绝对。而对于多站N2转移患者,即使技术上能切除,但鉴于其潜在播散风险高,长期预后差,2023年美国胸外科协会共识不推荐此类患者直接手术,部分欧美医生也会选择转诊至肿瘤放疗科。但随着免疫治疗的兴起,此类患者在新辅助治疗后如实现肿瘤降期,仍可重新评估切除可能。
可手术(Operable)侧重患者整体状况:能否耐受手术。即使肿瘤可切除,若患者心肺功能无法承受手术,仍属“不可手术”。肺功能评估核心是 “术后残余肺功能能否维持正常生活”,肺叶切除一般要求术前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(FEV1)> 1.5L,全肺切除要求FEV1 > 2.0L。更科学的方法是计算术后FEV1或肺一氧化碳弥散量(DLCO)占预计值百分比(PPO),国际指南建议PPO-FEV1或PPO-DLCO> 40%即代表手术风险可接受。临床中还需结合“综合评估”,如爬楼测试、血气分析、憋气时长等,避免仅依赖肺功能仪数据(部分患者操作不规范导致误差)。
最终,安全切除肿瘤并使患者获益是手术根本原则。
苏春霞 教授
您提到新辅助治疗可将“不可切除”转化为“可切除”,若本例患者存在ALK融合(这类肿瘤虽具侵袭性,但对ALK抑制剂反应好),若超适应症用了ALK-TKI且反应显著,这种情况下是否可考虑手术?
吴楠 教授
ALK融合确实是“钻石突变”,ALK通路在新辅助靶向治疗中比EGFR更具潜力。与EGFR抑制剂相比,ALK抑制剂的肿瘤退缩效果更突出,即使小样本研究也能看到积极信号:
2018年回顾性研究(11例N2患者,doi: 10.1016/j.jtho.2018.10.161):克唑替尼新辅助治疗,90%患者实现PR,90%实现R0切除,18%达pCR;
NAUTIKA1研究:阿来替尼新辅助的pCR率达33%;
ALNEO研究(33例):阿来替尼新辅助后,86%实现R0切除,12%达pCR。
虽暂无大型3期研究,但这些结果提示:ALK融合患者若超指南使用抑制剂后肿瘤降期,可重新评估手术可能。临床中我会建议这类患者优先纳入ALK抑制剂新辅助的临床研究,观察肿瘤反应后再决策。期待未来更多更重要的数据信息来支撑这样的一种治疗模式。
苏春霞 教授
很有趣的方向。朱教授,若此患者最终判定为不可切除IIIA期NSCLC,指南标准治疗方法是同步放化疗。您的团队将如何制定诊疗计划?对心肺功能有何要求?
朱正飞 教授
不可切除IIIA期NSCLC的标准方案是“同步放化疗+免疫巩固”(Pacific模式),诊疗计划需兼顾“技术可行性”与“患者耐受性”:
技术层面:需确保肿瘤能接受根治剂量(如60 Gy/30次),同时周围危及器官(如肺、心脏、食管、脊髓)受量在安全范围内。这与设备、物理师能力相关。
患者耐受性:放疗对肺功能要求通常低于手术。一般认为FEV1 > 0.75L或爬楼能力尚可(如能爬3层)即可。另外需评估是否存在间质性肺病或巨大肺大泡等基础病,后者可能增加放疗后破裂风险。此外,驱动突变状态会影响方案:若驱动基因阳性,可短期应用靶向药缩瘤,但不宜过长,以免增加肺损伤风险(尤其EGFR突变患者);野生型患者不建议诱导阶段过早联合免疫,以免放疗杀伤激活的T细胞,序贯放化疗后再免疫巩固是合理策略(基于GEMSTONE-301、PACIFIC-6等研究)。
苏春霞 教授
本例患者接受紫杉醇+卡铂联合根治性放疗后疗效良好,但初始脑MRI未用造影剂,放化疗后复查(用造影剂)发现右侧额顶叶1 cm脑转移。对这种寡转移,朱教授您的治疗决策是什么?若选择立体定向放射外科(SRS),如何评估治疗时机?
朱正飞 教授
孤立性脑转移的治疗需结合“病灶特征、患者状态、颅外控制情况”综合决策:
首选手术的情况:患者预期生存期长、颅外病灶控制良好、手术可安全切除(如非功能区病灶);手术优势在于局部控制率高,还能获取病理(排除原发脑肿瘤或其他转移),甚至通过基因检测明确脑转移灶与原发灶的突变差异,指导后续治疗。
首选SRS/SRT的情况:若患者不愿手术或位置不佳。我更倾向于大分割立体定向放疗(SRT,3-5次)而非单次SRS(伽马刀)。现代技术无需有创头架,分次治疗在生物效应和毒性方面可能更具优势。
SRS/SRT时机需结合“驱动突变状态”:
驱动突变阳性:若药物治疗对脑转移有效,可先用药至肿瘤最大退缩,再行放疗——此时病灶最小,放疗对正常脑组织的损伤也最小;
驱动突变阴性:若免疫/化疗对脑转移疗效有限、症状重、肿瘤负荷大的患者,需在脱水、激素对症治疗的同时尽早启动放疗,避免病灶进展。
苏春霞 教授
患者可能关注“质子治疗”这类高端放疗技术,质子治疗在此场景价值如何?
朱正飞 教授
质子治疗优势主要在于物理学效应(形成Bragg峰[布拉格峰]),能在肿瘤处形成高剂量后迅速下降,理论上能减少正常组织损伤。但需客观看待其价值:对小病灶,光子SRS/SRT已能实现很好疗效和保护,质子优势可能不足以颠覆常规选择。如同优等生,考91分与92分差别不大。但对于较大肿瘤或毗邻关键结构需极致保护的情况,质子治疗可能有其价值。
苏春霞 教授
新辅助治疗发展迅速,若患者接受新辅助放化疗,放疗是否会增加手术复杂性和风险?
吴楠 教授
确实会增加挑战。放疗后的手术挑战主要来自“组织改变”:约20%患者出现炎症反应,部分患者有纤维化,导致组织弹性下降、术中分离困难,甚至术后出现支气管残端瘘。既往INT0139研究显示,III期患者新辅助放化疗后行全肺切除,30天死亡率达20%-25%(远远高于未放疗组),尤其右全肺切除风险极高。但随着放疗技术进步(如放疗照射野的精准控制)以及免疫联合疗法的应用,安全性数据已在改善。未来需要MDT团队(外科与放疗科)紧密合作,探索最佳剂量、靶区和手术时机,以期患者获益最大化。
苏春霞 教授
临床中部分患者术后病理才发现N2阳性,此时MDT常讨论是否行术后放疗。朱教授,您如何看待术后放疗(PORT)?
朱正飞 教授
LungART研究以及中国的PORT-C研究均表明,不加选择地对所有术后pN2患者行PORT无生存获益。目前也尚未明确哪些特殊高危患者能从术后放疗中获益,需更多研究探索。
在当今免疫治疗时代,若患者已从新辅助免疫治疗中获益,再行纵隔淋巴结放疗,可能损伤残留的正常免疫细胞,影响后续免疫疗效。因此,目前PORT仅推荐在临床研究中进行,不用于常规实践。
专家简介

苏春霞 教授
教授,主任医师,博士生/博士后导师
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肿瘤综合诊治中心主任
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
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/上海市东方英才计划拔尖项目
美中抗癌协会USCACA Co-President联席主席
国际肺癌协作组织多学科协作委员会委员
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青年委员
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肿瘤临床转化研究专委会主委
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委会常委兼秘书长
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患者教育专委会副主委
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转化专委会、免疫治疗专委会常委
中国医促会肿瘤免疫治疗学分会常委
上海市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副理事长

吴楠 教授
教授、主任医师、博士生导师
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
入选国家级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项目
曾任国际肺癌研究协会(IASLC)会员委员会主席,现任IASLC会员委员会和分期委员会委员
欧洲肺癌大会(ELCC)学术委员会委员
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委员
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分会常委,肿瘤多学科诊疗专委会常委
中国临床肿瘤学会(CSCO)智慧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,非小细胞肺癌专委会委员
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瘤化学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
北京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副主委,胸外科分会常委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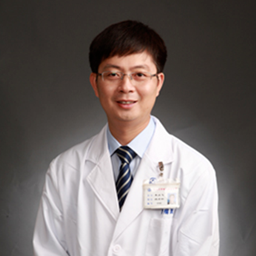
朱正飞 教授
教授、主任医师、博士生导师
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射治疗中心副主任
复旦大学胸部肿瘤研究所副所长
中国抗癌协会(CACA)肿瘤放射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、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、食管癌专业委员会委员
中华医学会肿瘤放射治疗分会青委
中国临床肿瘤学会(CSCO)非小细胞肺癌专委会委员
上海市医师协会肿瘤放射科医师分会副会长
中国医药教育学会肿瘤放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
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肺部肿瘤慢性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
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,上海市卫健委“医苑新星”杰出青年医学人才计划
获上海市抗癌科技奖一等奖(第一完成人)
MD. Anderson肿瘤中心访问学者
更多节目信息请前往以下网站了解
国际肺癌研究协会(IASLC)官方网址:
https://www.iaslc.org/
播客《Lung Cancer Considered》官方网址:
https://www.iaslc.org/LungCancerConsidered
编辑:lagertha
审核:苏春霞教授
来源:肿瘤界